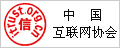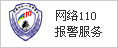經濟危機是“破壞性創新”的恰當時機
http://www.xibaipo.cc 2008-11-26 14:02 中企顧問網
本文導讀:經濟危機是“破壞性創新”的恰當時機,提供能源礦產、石油化工、IT通訊、房產建材、機械設備、電子電器、食品飲料、農林牧漁、旅游商貿、醫藥保艦交通物流、輕工紡織等行業專業研究報告
盡管全球化見證了美國在制造業、能源領域甚至金融業優勢地位的衰落,不過人們認為,有一點是無法攻克的,那就是:美國人的獨創性這一優良傳統。
只是現在看來這一點也不是安全無憂了。中國的工業一直讓西方羨慕的是其堅韌精神,而不是其獨創性,但現在,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個跨越多年的計劃,以使自己更有創新性、從而也將更具競爭力。新加坡也一樣。明年,芬蘭將會將本國的頂級商學院、設計學院和技術學院合并到一起,建立一所跨學科的“創新大學”。
美國國家科學總院(National Academies)于2007年出版了一份長達600頁的報告《站在即將來臨的風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該報告稱,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理事會成員“表達了這樣的憂慮:美國的科學和技術的削弱,不可避免地會使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惡化,尤其會削弱民眾在高端工作機會上的競爭力。”
近來,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創新領域——也就是對科學、技術和商業領域先進思想的推進——將會發生什么變化,要知道,全球經濟現在已陷于混亂狀態。傳統觀念或許以為,企業界、政府和學術界不太愿意接受與創新相伴的風險與短期花費。
不過,麥克技術創新中心(Mack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學術主任保羅·舒美克(Paul J.H.Schoemaker)則認為,對某些公司而言,經濟危機實際上為創新提供了一個平臺。“這場危機有多重影響。”舒梅科說。“收入和利潤的損失首先會使人產生削減成本的心理,這種心理對創新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一個病人正在流血,那么,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為他止血。隨之而來的步驟是企業領導者會提問,他們會重新思考商業模式的哪些部分是薄弱(從而可能無法維持下去)的,而這些思考則可以引發商業模式的重組和重建。
他還告誡說,要防止謹小慎微,也就是說,要避免過度依賴與變革性創新或者稱為“破壞性”創新相反的漸進性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在創新領域,這兩種創新方式——漸進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以“小我”創新和“大我”創新區別開來。舒美克說:“企業的最大收益,來自向固有模式和組織發起挑戰的那些更為大膽的創新。”
關于破壞性
雖然“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稱為“顛覆性創新”)這一短語成為辦公室的談資不過只有10年的時間,不過這一思想卻很有歷史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就曾借用“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一短語來描述他的關于企業家如何支撐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
那么,一個企業家或者一家企業如何才能具有“破壞性”呢?一個人怎么才能向投資者或者企業的上層證實某個激進的想法值得投資呢?
有一個人深諳將破壞性創新引向市場之道,他就是阿爾卡特-朗訊公司貝爾實驗室(Bell Labsat Alcatel-Lucent)的總裁金鐘勛(Jeong Kim),他同時也是位成功的技術型企業家。最近,他在一個題為《為破壞性創新鋪平道路》(Paving the Way for 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演講中提出了某些建議,這次演講是技術高管碩士課程(Executive Master′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簡稱EMTM)系列演講“新興技術與企業的整合”(Aligning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中的一部分。
在一個管理者所能擁有的最關鍵的資產中,他說,是公司普遍都認識到,破壞性創新非常重要。對于一個已經非常成功的企業,或者是對于一個官僚氣氛濃厚阻止創新出現的組織來說,這一點非常困難。公司還必須真正投入到科研中。“破壞性研究非常重要,在技術領域尤其如此。”
另外,單單擁有才華橫溢的工程師還是不夠的。如果企業中沒有適當的管理機制,那么,大部分出色的技術都會被扔進企業經營歷史的垃圾堆,甚至更糟糕的,會被競爭對手纂奪:“僅有破壞性創新還是不夠的。”金鐘勛說。“你可以列舉出很多這樣的實例:公司發明了新技術,但其地位最后卻被其他人取代了。”
按創新界的行話來說,這里提到的“其他人”就是“快速跟進者”(Fast Follower)(也稱為“快速模仿者”),快速跟進者是指擁有更好的資金條件、更敏銳的管理意識,在市場中能比原創者更快、更有效地開發利用某項技術的公司。“你可能是開發新技術的第一人,”金鐘勛說,“但是,只有商業模式更靈活、商業模式更具創新性的公司,才能更長久地保有競爭優勢。”
這一觀點引出了下面的問題:促進創新的最佳商業模式是什么呢?《沃頓論新興技術管理》(Wharton on Man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一書的合著者舒美克談到,事實上,現有的很多決策工具可以幫助企業系統性地管理創新項目。
舒美克認為,創新的過程類似于打霰彈槍,而不是步槍。因為創新項目的失敗率很高,所以,公司明智的做法應該是考慮到多種可能性和偶然性,而不是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某一個計劃上面。“只管自己的事情”(Sticking to our knitting)似乎是頗為受用的商業箴言,對很多從dot.com時代挺過來的公司來說,這個箴言也確實很靈驗。但是,舒美克和其他創新權威則主張,企業應該把與自身行業相鄰的領域當作創新突破的沃土。線性的舊有創新方式主要依賴于標準化的測試方案,而只依賴這種方式的創新方法往往是過時的。“通過檢視公司的成長鴻溝(Growth Gap)、發展方案、探尋相鄰領域以及向‘藍海’更勇敢進發的方式,公司可以收獲更多的利潤。”舒梅科說。(“藍海”(Blue Oceans)是創新者對尚未實現的、因此也是尚不存在競爭的市場的稱謂。)“然而,投資的方式必須要更多地著眼于選擇性戰略和投資組合戰略,而不要拘泥于靜止的‘凈現值’(Net Present Value,簡稱NPV)評估方法。”
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瑪麗·本納(Mary Benner)認為,“只管自己的事情”的心態會對大公司應對競爭威脅的能力造成侵害。“我發現,在公司的股東和證券分析家看來,公司在新技術上的大膽創新或者向新市場進發的行為,遠離了他們對公司的期望。投資者和證券分析家通常更希望公司通過‘只管自己的事情’的方式,來使股東的價值最大化。結果就是,大型公司,尤其是那些人們認為擁有穩定的、可預期盈利和紅利的公司——也就是‘績優股公司’——向新技術領域進發的行為,或者進行顛覆性創新的行為,往往不太可能在股票市場中受到褒獎,相反,它們很可能會受到股價下跌以及市值減少的懲罰。”
她談到,她在研究中發現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電信巨頭弗萊森電訊公司(Verizon Communications)的情況。股票分析家對弗萊森電訊公司在FiOS上的大筆投資提出了質疑,FiOS是一種高通量的光纖網絡,該項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康姆卡斯特公司(Comcast)的有線電視、高速互聯網和網絡語音電話服務的“三重服務”(Triple-Play)(也稱為“三網融合業務”、“三網合一服務”,即語音、視頻和互聯網接入服務。)對自己業務的威脅。
“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并不擅長評估那些無形的、難以預測的創新以及技術變革的價值。”本納說。“對大型上市公司而言,這就意味著它們在從事顛覆性創新時可能會處于劣勢,相反,有風險投資支持的初創型企業更容易產生這樣的創新。”
確實,在不遠的將來,將創新本身外包可能會成為一個潮流。“尤其是在制藥領域,企業購買由私有資金資助的小型企業——比如,生物技術初創型公司——完成的創新成果,已經成了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本納說。“或許,很多顛覆性創新活動的場地,將會從大型組織向小型初創型企業轉移。”
沃頓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麥克技術創新中心的聯席主任、《沃頓論新興技術管理》一書的合著者喬治·戴伊(George S.Day)認為,這種現象讓人們注意到了在產品開發領域正在出現的一個“大趨勢”,那就是“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開放式創新也稱為“眾包”(Crowdsourcing)(“眾包”是指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眾網絡的做法。眾包的任務通常由個人來承擔,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協作才能完成的任務,也有可能以依靠開源的個體生產的形式出現。——譯者注),為解決企業的問題,這種創新方式需要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通力協作。
眾包模式的典型就是設在馬薩諸塞州沃爾瑟姆(Waltham)的“創新中心”(Inno Centive)網站。該網站能將遇到科學問題、工程技術問題和商業問題的公司——即“尋求者”(Seeker)——與全球的業余“解決者”(Solver)匹配起來。之后,“解決者”為了競爭自夸的權利,更經常地是為了競爭虛擬貨幣,而為給公司遇到的問題提供最佳答案。“大部分公司并不是要尋求能讓自己擊敗對手的重要創新成果,”戴伊說,相反,它們只是想為某個大難題中的一個特定的小問題尋求快捷的答案。
金鐘勛認為,對那些希望自己的“密制調料”始終要來自企業內部的公司來說,之前取得的成功可能會成為創新的重大障礙。問題在于,以前的成功形成了一種“虛擬模式”,也就是說形成了一種“如何做事”的固定范式,而新思想在這種模式中是無法繁榮起來的。金鐘勛將其稱之為“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他說,組建跨學科團隊“是打破知識詛咒的一個有效途徑。”另一條有效途徑是“經驗配對”,也就是讓一位資深員工,與一個經驗少得多、但就如何解決問題有很多新想法的員工配對工作。
金鐘勛說,破壞性創新一個絕佳的機會隱藏在“信息超載”這一問題中。知識的創造速度,遠遠超過了任何人的吸收速度。這種狀況的另一面就是我們要不斷過濾海量的信息,因為我們總是受到規模空前的信息的轟炸。
為了證實自己的這一觀點,金鐘勛給聽眾們展示了一個電影片段,這是重復一個古老心理實驗的電影剪輯。有兩支球隊,一支球隊身穿白色運動衣,另一支球隊穿黑色運動衣,隊員們在場上在不斷運球、傳球。聽眾被告知,要計算穿黑色運動衣的球員的傳球次數。很少有學生會注意到,裝扮成大猩猩的一個人曾若無其事地從球場中間穿過,因為他們并不是在尋求這樣的信息。“我敢肯定,你們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個‘大猩猩’,但是,有些人注意到了,并記住了,有些人則視而不見,因為你們在尋找某個特定的東西。”
7小時的“急流泛舟”
20世紀90年代末,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的著作《創新者的困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出版以后,“破壞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y)(也稱為“顛覆性技術”)這一短語漸漸流行開來。但實際上,自1925年創建以來,作為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和西方電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的合資機構,貝爾實驗室一直在扮演著創新方式轉化以及“破壞性”創新孵化器的角色。
設在新澤西州北部的貝爾實驗室已經獲得了六次諾貝爾獎,因其系列創新成果而獲得了廣泛的贊譽:光電池、硅晶體管、統計過程控制(SPC)、UNIX操作系統、C程序語言、數字電話技術以及無線局域網技術,就是在貝爾實驗室完成的幾項廣受好評的創新成果。
金鐘勛說,今天,貝爾實驗室的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同樣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創新工作。比如,他們現在正在開發能根據電壓而轉變成任何形狀的液體傳感器,金鐘勛設想,這種產品可以當作可變焦鏡頭來使用。此外,這一研發部門還開發出了利用納米技術創作3D影像的技術。“你在3D科幻電影中看到過全息電影吧?那種效果是可以制作出來的,現在,利用這些技術就能制作。而且成本也不高。”
金鐘勛談到了阿爾卡特-朗訊公司——當時是朗訊科技公司——如何將破壞性創新的精神,注入到死水一潭的文化環境中的一個案例。朗訊科技公司光網絡部門的表現很差,公司解雇了這個部門的高層經理。“我確信,我被安插到那里的原因是沒有其他人愿意去,另外,他們也需要找個人當出氣筒。”金鐘勛說。
這個部門已經瀕臨死亡:財務表現讓人大失所望,而且士氣低落。金鐘勛重組了管理團隊,讓留用的人參加一個以“急流泛舟”為特色的外出靜思會(Off-Site Retreat)。“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說‘為什么我們要做……?’沒過一會兒,大家就感到厭煩不已了。”這個練習旨在強化團隊精神和協作精神,是在一位心理學家的幫助下設計而成的。經理們非但沒有協作起來,相反,他們開始用船槳相互濺水,就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漂流結束以后,這項心理練習實驗并沒有結束。“六七個小時的急流泛舟以后,他們都很疲勞了。”在當天晚上的餐桌上,人們放下了工作中的謹慎,把時間用來彼此了解。
就像人們想到的,第二天的活動是“離場戰略規劃”和“白板交流”,但是,金鐘勛說,比起他們前一天彼此形同陌路的狀態來,這一天的互動變得更真誠也更富成效了。他說,那次靜思會以后的第一個季度,這個群體創造了5.1億美元的收入,接下來的一個季度,收入增長到了5.6億美元,之后是7.3億美元,再之后達到了9.7億美元。他補充說,關鍵在于“對公司的成功而言,團隊精神是絕對至關重要的。”
金鐘勛告誡說,發動破壞性創新并不是革命,盡管在很多公司依然拘泥于季度對季度的考評方法、員工也多抱有類似的短期觀點的情況下,這種創新方式看似頗為稀有。
現在看來,即使著名的貝爾實驗室也無法避免要快速推出實用技術的壓力。讓科學界震驚的是,今年夏天,阿爾卡特-朗訊公司幾乎斷絕了給予基礎物理學研究的資金支持。公司的官員稱,這一行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實驗室與母公司在無線技術、光學技術、網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商業需要更加密切地統一起來。正如阿爾克特-朗訊公司的發言人彼得·本尼迪克特(Peter Benedict)8月對《連線雜志》(Wired Magazine)雜志談到的:“在全新的創新模式中,研究工作要專注于母公司的需要。”
基礎研究是對科學問題最基本法則的研究,與商業應用沒有直接聯系。然而,基礎研究又是我們今天享受到的大部分現代技術產品——比如,商業航空、全球定位系統(GPS)和激光等——的根基。
“你必須要投入資金,要提高人類的知識,要建立網絡,”金鐘勛說,“這才是領先之道。”
只是現在看來這一點也不是安全無憂了。中國的工業一直讓西方羨慕的是其堅韌精神,而不是其獨創性,但現在,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個跨越多年的計劃,以使自己更有創新性、從而也將更具競爭力。新加坡也一樣。明年,芬蘭將會將本國的頂級商學院、設計學院和技術學院合并到一起,建立一所跨學科的“創新大學”。
美國國家科學總院(National Academies)于2007年出版了一份長達600頁的報告《站在即將來臨的風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該報告稱,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理事會成員“表達了這樣的憂慮:美國的科學和技術的削弱,不可避免地會使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惡化,尤其會削弱民眾在高端工作機會上的競爭力。”
近來,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創新領域——也就是對科學、技術和商業領域先進思想的推進——將會發生什么變化,要知道,全球經濟現在已陷于混亂狀態。傳統觀念或許以為,企業界、政府和學術界不太愿意接受與創新相伴的風險與短期花費。
不過,麥克技術創新中心(Mack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學術主任保羅·舒美克(Paul J.H.Schoemaker)則認為,對某些公司而言,經濟危機實際上為創新提供了一個平臺。“這場危機有多重影響。”舒梅科說。“收入和利潤的損失首先會使人產生削減成本的心理,這種心理對創新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一個病人正在流血,那么,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為他止血。隨之而來的步驟是企業領導者會提問,他們會重新思考商業模式的哪些部分是薄弱(從而可能無法維持下去)的,而這些思考則可以引發商業模式的重組和重建。
他還告誡說,要防止謹小慎微,也就是說,要避免過度依賴與變革性創新或者稱為“破壞性”創新相反的漸進性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在創新領域,這兩種創新方式——漸進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以“小我”創新和“大我”創新區別開來。舒美克說:“企業的最大收益,來自向固有模式和組織發起挑戰的那些更為大膽的創新。”
關于破壞性
雖然“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稱為“顛覆性創新”)這一短語成為辦公室的談資不過只有10年的時間,不過這一思想卻很有歷史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就曾借用“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一短語來描述他的關于企業家如何支撐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
那么,一個企業家或者一家企業如何才能具有“破壞性”呢?一個人怎么才能向投資者或者企業的上層證實某個激進的想法值得投資呢?
有一個人深諳將破壞性創新引向市場之道,他就是阿爾卡特-朗訊公司貝爾實驗室(Bell Labsat Alcatel-Lucent)的總裁金鐘勛(Jeong Kim),他同時也是位成功的技術型企業家。最近,他在一個題為《為破壞性創新鋪平道路》(Paving the Way for 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演講中提出了某些建議,這次演講是技術高管碩士課程(Executive Master′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簡稱EMTM)系列演講“新興技術與企業的整合”(Aligning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中的一部分。
在一個管理者所能擁有的最關鍵的資產中,他說,是公司普遍都認識到,破壞性創新非常重要。對于一個已經非常成功的企業,或者是對于一個官僚氣氛濃厚阻止創新出現的組織來說,這一點非常困難。公司還必須真正投入到科研中。“破壞性研究非常重要,在技術領域尤其如此。”
另外,單單擁有才華橫溢的工程師還是不夠的。如果企業中沒有適當的管理機制,那么,大部分出色的技術都會被扔進企業經營歷史的垃圾堆,甚至更糟糕的,會被競爭對手纂奪:“僅有破壞性創新還是不夠的。”金鐘勛說。“你可以列舉出很多這樣的實例:公司發明了新技術,但其地位最后卻被其他人取代了。”
按創新界的行話來說,這里提到的“其他人”就是“快速跟進者”(Fast Follower)(也稱為“快速模仿者”),快速跟進者是指擁有更好的資金條件、更敏銳的管理意識,在市場中能比原創者更快、更有效地開發利用某項技術的公司。“你可能是開發新技術的第一人,”金鐘勛說,“但是,只有商業模式更靈活、商業模式更具創新性的公司,才能更長久地保有競爭優勢。”
這一觀點引出了下面的問題:促進創新的最佳商業模式是什么呢?《沃頓論新興技術管理》(Wharton on Man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一書的合著者舒美克談到,事實上,現有的很多決策工具可以幫助企業系統性地管理創新項目。
舒美克認為,創新的過程類似于打霰彈槍,而不是步槍。因為創新項目的失敗率很高,所以,公司明智的做法應該是考慮到多種可能性和偶然性,而不是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某一個計劃上面。“只管自己的事情”(Sticking to our knitting)似乎是頗為受用的商業箴言,對很多從dot.com時代挺過來的公司來說,這個箴言也確實很靈驗。但是,舒美克和其他創新權威則主張,企業應該把與自身行業相鄰的領域當作創新突破的沃土。線性的舊有創新方式主要依賴于標準化的測試方案,而只依賴這種方式的創新方法往往是過時的。“通過檢視公司的成長鴻溝(Growth Gap)、發展方案、探尋相鄰領域以及向‘藍海’更勇敢進發的方式,公司可以收獲更多的利潤。”舒梅科說。(“藍海”(Blue Oceans)是創新者對尚未實現的、因此也是尚不存在競爭的市場的稱謂。)“然而,投資的方式必須要更多地著眼于選擇性戰略和投資組合戰略,而不要拘泥于靜止的‘凈現值’(Net Present Value,簡稱NPV)評估方法。”
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瑪麗·本納(Mary Benner)認為,“只管自己的事情”的心態會對大公司應對競爭威脅的能力造成侵害。“我發現,在公司的股東和證券分析家看來,公司在新技術上的大膽創新或者向新市場進發的行為,遠離了他們對公司的期望。投資者和證券分析家通常更希望公司通過‘只管自己的事情’的方式,來使股東的價值最大化。結果就是,大型公司,尤其是那些人們認為擁有穩定的、可預期盈利和紅利的公司——也就是‘績優股公司’——向新技術領域進發的行為,或者進行顛覆性創新的行為,往往不太可能在股票市場中受到褒獎,相反,它們很可能會受到股價下跌以及市值減少的懲罰。”
她談到,她在研究中發現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電信巨頭弗萊森電訊公司(Verizon Communications)的情況。股票分析家對弗萊森電訊公司在FiOS上的大筆投資提出了質疑,FiOS是一種高通量的光纖網絡,該項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康姆卡斯特公司(Comcast)的有線電視、高速互聯網和網絡語音電話服務的“三重服務”(Triple-Play)(也稱為“三網融合業務”、“三網合一服務”,即語音、視頻和互聯網接入服務。)對自己業務的威脅。
“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并不擅長評估那些無形的、難以預測的創新以及技術變革的價值。”本納說。“對大型上市公司而言,這就意味著它們在從事顛覆性創新時可能會處于劣勢,相反,有風險投資支持的初創型企業更容易產生這樣的創新。”
確實,在不遠的將來,將創新本身外包可能會成為一個潮流。“尤其是在制藥領域,企業購買由私有資金資助的小型企業——比如,生物技術初創型公司——完成的創新成果,已經成了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本納說。“或許,很多顛覆性創新活動的場地,將會從大型組織向小型初創型企業轉移。”
沃頓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麥克技術創新中心的聯席主任、《沃頓論新興技術管理》一書的合著者喬治·戴伊(George S.Day)認為,這種現象讓人們注意到了在產品開發領域正在出現的一個“大趨勢”,那就是“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開放式創新也稱為“眾包”(Crowdsourcing)(“眾包”是指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眾網絡的做法。眾包的任務通常由個人來承擔,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協作才能完成的任務,也有可能以依靠開源的個體生產的形式出現。——譯者注),為解決企業的問題,這種創新方式需要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通力協作。
眾包模式的典型就是設在馬薩諸塞州沃爾瑟姆(Waltham)的“創新中心”(Inno Centive)網站。該網站能將遇到科學問題、工程技術問題和商業問題的公司——即“尋求者”(Seeker)——與全球的業余“解決者”(Solver)匹配起來。之后,“解決者”為了競爭自夸的權利,更經常地是為了競爭虛擬貨幣,而為給公司遇到的問題提供最佳答案。“大部分公司并不是要尋求能讓自己擊敗對手的重要創新成果,”戴伊說,相反,它們只是想為某個大難題中的一個特定的小問題尋求快捷的答案。
金鐘勛認為,對那些希望自己的“密制調料”始終要來自企業內部的公司來說,之前取得的成功可能會成為創新的重大障礙。問題在于,以前的成功形成了一種“虛擬模式”,也就是說形成了一種“如何做事”的固定范式,而新思想在這種模式中是無法繁榮起來的。金鐘勛將其稱之為“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他說,組建跨學科團隊“是打破知識詛咒的一個有效途徑。”另一條有效途徑是“經驗配對”,也就是讓一位資深員工,與一個經驗少得多、但就如何解決問題有很多新想法的員工配對工作。
金鐘勛說,破壞性創新一個絕佳的機會隱藏在“信息超載”這一問題中。知識的創造速度,遠遠超過了任何人的吸收速度。這種狀況的另一面就是我們要不斷過濾海量的信息,因為我們總是受到規模空前的信息的轟炸。
為了證實自己的這一觀點,金鐘勛給聽眾們展示了一個電影片段,這是重復一個古老心理實驗的電影剪輯。有兩支球隊,一支球隊身穿白色運動衣,另一支球隊穿黑色運動衣,隊員們在場上在不斷運球、傳球。聽眾被告知,要計算穿黑色運動衣的球員的傳球次數。很少有學生會注意到,裝扮成大猩猩的一個人曾若無其事地從球場中間穿過,因為他們并不是在尋求這樣的信息。“我敢肯定,你們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個‘大猩猩’,但是,有些人注意到了,并記住了,有些人則視而不見,因為你們在尋找某個特定的東西。”
7小時的“急流泛舟”
20世紀90年代末,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的著作《創新者的困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出版以后,“破壞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y)(也稱為“顛覆性技術”)這一短語漸漸流行開來。但實際上,自1925年創建以來,作為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和西方電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的合資機構,貝爾實驗室一直在扮演著創新方式轉化以及“破壞性”創新孵化器的角色。
設在新澤西州北部的貝爾實驗室已經獲得了六次諾貝爾獎,因其系列創新成果而獲得了廣泛的贊譽:光電池、硅晶體管、統計過程控制(SPC)、UNIX操作系統、C程序語言、數字電話技術以及無線局域網技術,就是在貝爾實驗室完成的幾項廣受好評的創新成果。
金鐘勛說,今天,貝爾實驗室的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同樣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創新工作。比如,他們現在正在開發能根據電壓而轉變成任何形狀的液體傳感器,金鐘勛設想,這種產品可以當作可變焦鏡頭來使用。此外,這一研發部門還開發出了利用納米技術創作3D影像的技術。“你在3D科幻電影中看到過全息電影吧?那種效果是可以制作出來的,現在,利用這些技術就能制作。而且成本也不高。”
金鐘勛談到了阿爾卡特-朗訊公司——當時是朗訊科技公司——如何將破壞性創新的精神,注入到死水一潭的文化環境中的一個案例。朗訊科技公司光網絡部門的表現很差,公司解雇了這個部門的高層經理。“我確信,我被安插到那里的原因是沒有其他人愿意去,另外,他們也需要找個人當出氣筒。”金鐘勛說。
這個部門已經瀕臨死亡:財務表現讓人大失所望,而且士氣低落。金鐘勛重組了管理團隊,讓留用的人參加一個以“急流泛舟”為特色的外出靜思會(Off-Site Retreat)。“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說‘為什么我們要做……?’沒過一會兒,大家就感到厭煩不已了。”這個練習旨在強化團隊精神和協作精神,是在一位心理學家的幫助下設計而成的。經理們非但沒有協作起來,相反,他們開始用船槳相互濺水,就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漂流結束以后,這項心理練習實驗并沒有結束。“六七個小時的急流泛舟以后,他們都很疲勞了。”在當天晚上的餐桌上,人們放下了工作中的謹慎,把時間用來彼此了解。
就像人們想到的,第二天的活動是“離場戰略規劃”和“白板交流”,但是,金鐘勛說,比起他們前一天彼此形同陌路的狀態來,這一天的互動變得更真誠也更富成效了。他說,那次靜思會以后的第一個季度,這個群體創造了5.1億美元的收入,接下來的一個季度,收入增長到了5.6億美元,之后是7.3億美元,再之后達到了9.7億美元。他補充說,關鍵在于“對公司的成功而言,團隊精神是絕對至關重要的。”
金鐘勛告誡說,發動破壞性創新并不是革命,盡管在很多公司依然拘泥于季度對季度的考評方法、員工也多抱有類似的短期觀點的情況下,這種創新方式看似頗為稀有。
現在看來,即使著名的貝爾實驗室也無法避免要快速推出實用技術的壓力。讓科學界震驚的是,今年夏天,阿爾卡特-朗訊公司幾乎斷絕了給予基礎物理學研究的資金支持。公司的官員稱,這一行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實驗室與母公司在無線技術、光學技術、網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商業需要更加密切地統一起來。正如阿爾克特-朗訊公司的發言人彼得·本尼迪克特(Peter Benedict)8月對《連線雜志》(Wired Magazine)雜志談到的:“在全新的創新模式中,研究工作要專注于母公司的需要。”
基礎研究是對科學問題最基本法則的研究,與商業應用沒有直接聯系。然而,基礎研究又是我們今天享受到的大部分現代技術產品——比如,商業航空、全球定位系統(GPS)和激光等——的根基。
“你必須要投入資金,要提高人類的知識,要建立網絡,”金鐘勛說,“這才是領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