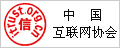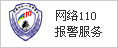長安街拓寬改造 拆遷區域每平米補償30706元
http://www.xibaipo.cc 2009-04-21 15:10 中企顧問網
本文導讀:“工程與建國60周年慶典沒有必然聯系。”孟慶利說,該項目完成后將全面實現長安街整體規劃,提升交通承載能力。“長安街新華門段由于路窄,經常出現擁堵。拆遷完成后,這一段將由目前的雙向8車道拓寬為雙向10車道,交通將得到改善。”
73歲的王大媽即將告別居住了近40年的老屋。老屋位于西長安街南側的雙柵欄胡同一號,是個大雜院,屋后不遠就是每天車流滾滾的長安街。
進了院門往里走,走過搭建在路旁的一間窄窄的廚房,就是王大媽的住房。房間里有一張床、一張沙發、一張方桌和一個柜子,柜子里放著些鍋碗瓢盆,中間是一臺21寸舊彩電。
王大媽的日常生活都集中在這間房子里。她已經習慣了周圍的一切,包括每隔四五分鐘地鐵一號線給地板帶來的明顯震動。
離別總是難舍。“這兒多安全啊!”王大媽說。
在這里,晚飯后,王大媽可以悠然地到天安門遛彎兒;白玉蘭盛開的季節,她可以賞賞長安街上的玉蘭花;在這里甚至可以不用鐘表,因為斜對面電報大樓每到整點就會敲起響亮的鐘聲??
持續了幾十年的生活節奏,就要改變。
4月1日,西長安街道路拓寬拆遷工程進入施工階段。這一項目位于西城區西長安街新華門南側,東起石碑胡同,西至中組部辦公樓,北起長安街南沿線,南至西安福胡同、東安福胡同西段、東安福胡同東段南延50米。拆遷范圍內共有居民 778戶,單位42戶。
“這是唯一一段現存的老北京的長安街。”著名文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老字號的揖別
“六福居”是一家老餐廳,位于大六部口西北角。由于緊鄰長安街,這家飯館的生意一直不錯,經常需要等座。
4月初,本刊記者來到這里,餐廳已經搬離,大廳空空如也,“六福居”三個大字的“六”和“居”還在,“福”字卻已不見。旁邊一位老居民說:“這是把‘福’帶走,叫‘留福’呀!走到哪里,生意都能做得興旺!”
第一批搬離的還有攝貿金廣角,這是一家國營攝影器材店,上世紀80年代由崇文門搬到此地,被譽為京城第一代攝影發燒友的搖籃。
搬遷后,攝貿被拆分為幾部分,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距舊址不遠的北新華街6號。本刊記者找到這家新店的時候,攝貿金廣角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司長寶正在忙著進貨,安排新店的工作。“這一處的營業面積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他說。
至于有著102年歷史的西長安街郵局,如今已成平地。緊隨其后正在搬遷的,還有柳泉居豆包專賣店、老百信大藥房、張瑞林書法藝術院等。
處于拆遷區的安福胡同里流傳著兩段歷史故事。清朝乾隆皇帝寵愛來自新疆的香妃,因民族習慣不同,香妃不便住進皇宮,乾隆將她安置在寶月樓(今新華門處)居住。為了讓香妃能望見族人,以排遣鄉愁,乾隆安排香妃族人聚居在西長安街路南的街巷中,即今東安福胡同一帶,時稱“回回營”。
《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三載,乾隆御制寶月樓詩云:“鱗次居回部,安西系遠情。”據老居民介紹,胡同里原有一座清真寺,如今已經殘破,深鎖在一個院子里。不過如果在胡同里細心尋訪,仍可看到數百年前回部建筑的遺存---一段漢白玉拱門,拱門上精美的雕花,流露著濃郁的伊斯蘭風情。
北洋軍閥時期,安福胡同曾是盛極一時的段祺瑞(皖系)軍閥政治集團的大本營。1917年11月,段祺瑞為了進一步鞏固他的政治,在安福胡同布置了一個龐大的房舍,作為他那一派軍閥政客聚會之地,起名叫安福俱樂部。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政客就叫“安福系”。由這個派系操縱選舉的議會叫“安福議會”。這個派系控制北洋政府,從民國六年(1917)到民國九年(1920)。民國九年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失敗,安福俱樂部被封。
專家感到撓頭的花墻
安福胡同附近有許多名字帶“栓”字的胡同,如北小栓、南小栓、東小栓等。這與明代宮廷制度有關。明代,官員上朝、辦事,有的會騎馬來,但是宮廷中大臣不得騎馬,因而絕大多數的官員都要在長安右門外下馬、拴馬。直到今天,在胡同里走走,偶爾在民居的墻上還能看到拴馬環,斑斑的銹跡訴說著歷史過往。
不過,文物專家說,這個地段總體上文物價值不高。讓文物專家最感撓頭的是,如何處理矗立在這片民居與西長安街之間的那段灰色花墻。
這段長200米左右的花墻大有來頭。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政府接管了清室的西苑三海,并將中海和南海作為總統府,從那時起,中海和南海被合稱為“中南海”。
按中國傳統,府邸的正門要開在南面。袁世凱為了顯示總統府的規格氣派,將位于中南海南墻內僅幾米處的寶月樓下層當中三間打通,改建為大門。又將擋在門前的皇城紅墻扒開一段缺口,加砌了兩道“八字墻”,使缺口與大門銜接。改建后的寶月樓,被命名為“新華門”。
當時,新華門對面是一片雜亂破舊的老房,為改善總統府前的觀瞻,便砌筑了這道西洋式花墻。
這一系列工程,都是由當時的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朱啟鈐主持的。“墻與新華門之間的比例非常協調,設計很高明,突出了中南海。如果拆掉,新華門看上去會變小。”謝辰生說。
如何處理這堵保存十分完整的花墻,謝辰生說目前仍在研究中。一個方案是整體往南遷移,另一方案是原地保存。
中國著名古建筑學家羅哲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新的規劃如果說避不開這堵墻,搬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可以回避,就原地保護。好在目前并沒有人主張要完全拆除這堵墻。”
4月14日,本刊記者看到,花墻旁長安街邊的槐樹已經被砍伐。“太老的就不要了,樹齡小的會移到別的地方。”
高度重視的拆遷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孟慶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次采取政府主導的拆遷方式,由政府成立拆遷指揮部,統一指揮協調。
“工程與建國60周年慶典沒有必然聯系。”孟慶利說,該項目完成后將全面實現長安街整體規劃,提升交通承載能力。“長安街新華門段由于路窄,經常出現擁堵。拆遷完成后,這一段將由目前的雙向8車道拓寬為雙向10車道,交通將得到改善。”
在拆遷補償上,孟慶利介紹,此次拆遷首次按市場評估價格進行貨幣補償,評估經過專家認定,并得到市主管部門批準。本次拆遷區域內所有住宅房屋的補償基礎價格為每建筑平方米30706元。
為鼓勵居民在規定期限內盡早騰退房屋,拆遷指揮部還對提前搬家的居民采取獎勵措施。在4月6日前搬家騰房的居民,每戶給予提前搬家獎勵費2.5萬元,重點工程配合獎勵費5萬元,合計7.5萬元。
考慮到拆遷居民需要一段時期的搬家周轉,拆遷指揮部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標準進行一次性補助。拆遷居民還可獲得其他補助,包括移機費每部電話補助235元,有線電視費每戶補助300元,空調移機費每臺補助400元以及住宅房屋每平方米20元的搬家補助。另外,殘疾戶家庭和低保家庭將各得到3萬元補助。
4月10日,獎勵期已結束,孟慶利告訴本刊記者,簽了拆遷合同的大致是一半左右。
王大媽還在猶豫,“我的房子面積是28平米,按照補償價格我沒法在周圍地段買房子。”
孟慶利介紹,指揮部籌集了三處限價房源供被拆遷居民選購,分別是昌平區東小口的溪城家園(均價6500元/平方米),朝陽區常營的富力陽光美園(均價5900元/平方米),海淀區上地的美和園(均價6600元/平方米)。此外還提供了部分二手房、商品房等房源信息。
“那都是五六環以外了。”王大媽說,一個人住到郊區,看病不方便。她沒有退休金,因而算賬格外仔細,“住樓房要交物業費,用抽水馬桶還得交水費,樣樣都需要多花錢。”
據本刊記者了解,這個地區整體居住條件比較落后,戶均住房面積不足20平米,目前已經搬走的居民大多是拆遷面積較大的或者已經在其他地方購房的。
一條顯赫大街的60年
一項面對長安街行人的問卷調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
《望東方周刊》記者李靜|北京報道
1950年6月,為迎接新中國第一個國慶日,“林蔭大道”工程在長安街熱火朝天地開始了。根據規劃,從東單路口到西邊的府前街東口,在原有15米寬的瀝青路南北兩側,各修一條15米寬的新路,新路與舊路之間,種上了四排高大的喬木。
“當時我們參加拓馬路,還在王府井砌高臺,有兩三米高,同時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規劃學會理事長趙知敬,當時才上初中,作為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也參加了修建大道的“義務勞動”。
此時,一幅關于“長安街如何建設”的規劃藍圖也慢慢展開。
請蘇聯專家幫忙規劃
“解放后不久,蘇聯專家先做了一次規劃,圖畫得特別簡單,就一大條。”原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董光器翻開城建檔案,指向1949年蘇聯專家設計的長安街行政建筑設計圖。其中,蘇聯專家提出,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并沿長安街建設行政辦公樓。這一規劃的核心思想是將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區。
這一設想卻遭到中國本土專家的反對。1950年,梁思成、陳占詳刊印長達2.5萬字的“梁、陳方案”,其中特別提到沿長安街蓋行政大樓這種模式存在種種弊端,建議在西郊發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這樣,圍繞著‘行政中心區位置’的討論,全國建筑師聚集到北京,反復做規劃方案。”趙知敬回憶說,整個5 0年代對長安街的規劃,雖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紡織部、燃料部、工業部在蘇聯專家提議的空地上一一開工。隨著經濟形勢好轉,“今兒蓋一棟樓、明兒蓋一棟樓”。
北京急需一個整體規劃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聘請蘇聯專家指導。6月下旬,又指定了幾位老干部,抽調少數黨員青年技術干部,研究這個問題。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報了統一的城市規劃意見--- 《改建與擴建北京規劃草案要點》。
行政中心最終被確立在舊城,長安街作為“中央主要領導機關所在地”被明確提出。但長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規劃委員會工作的趙知敬回憶,那時,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規劃專業。于是決定邀請蘇聯專家來做詳細規劃。“我們當時就聽蘇聯專家講課,每天看蘇聯的教科書。”在“蘇聯專家結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
在這份方案中,長安街的藍圖基本繪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為“全國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長安街則肩負起全力體現這一主題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門和有全國意義的重大建筑,將沿長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馬路主義”
1958年方案的執筆者之一、時任北京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圖室主任的陳干,對長安街作為北京“東西軸線”的建設,滿心憧憬。他希望通過長安街的規劃,形成有別于紫禁城的軸線,與傳統的南北軸線相交于天安門廣場,確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點”(城市坐標)。
在趙知敬這些老北京心中,長安街能作為“東西軸線”是由它的歷史地位所決定的---它是北京舊城最寬的一條東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臨近天安門廣場。
長安街在歷史上正式的長度只有3.8公里,從東單到西單。“東單往東到建國門,西單往西到復興門都沒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幾個彎,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寬度。每天公共汽車在里面滿滿當當地開著。”趙知敬回憶說。
這樣的格局在1958年被徹底改變。國慶十周年前夕,西單到復興門的邱祖胡同等,東單到建國門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寬的瀝青路,復興門到建國門全線貫通,長安街長長了---6.7公里。道路徹底打通,為兩側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十年大慶為長安街的建設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在董光器看來,如果只有3.8公里,長安街根本沒法進行大規模建設。
在大規模建設的同時,一個禁區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動。事實上,從1952年拆除長安左門和右門開始,“古建筑的拆與保”的交鋒就在不斷上演,當長安街向著具有“首都風貌”的大干線思路發展,雙塔寺、牌樓這些古跡,都隨著不斷翻新的長安街景象,走入歷史。
由是,長安街的改造,在關注北京城變遷的記者王軍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槍”。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長安街呈現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長安街修起了80米寬的游行大道,擴建后的天安門前,形成了東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廣場---這種規模和氣勢,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象。
此時,長安街沿線的建筑,除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飯店、民族宮等,還有在長安街南邊的紡織部、煤炭部等部委辦公樓。這些莊嚴而肅穆的大廈,隨著國慶10周年,完成了長安街從規劃草圖走向現實的轉變。一條以政治形象聞名世界的大街,從此誕生。
然而,“第一槍”打出沒多久,便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來,國家大劇院沒建成,科技館也撂下了。”董光器回憶。直到1964年,經過三年調整,國力有些恢復。萬里作為北京市當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匯報,提出中央有一些辦公樓可以集中在長安街上蓋。
很快,北京市政府開始著手編制長安街規劃。1964年4月,長安街有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方案,特別是確定了包括道路寬度在內的具體原則。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長安街的馬路寬度一直難以確定。“50年代翻譯很多國外首都的資料,感覺到,作為首都的一條主要街道,道路過窄對交通影響很大。所以,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提出北京的馬路要寬。”
國家計委與北京市委的意見相左,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但北京市委的態度堅決,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會上表態:你說我是大馬路,我說你是小馬路主義。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是太寬,現在北京的汽車還不太多,等你們這些年輕人到八九十歲,北京有幾百萬輛車的時候,再看誰對誰錯。
到1954年,對長安街寬度有了初步定論: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終劃定為“120米”。“北京派出一個城市建設代表團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區的建設,回來一比較,發覺北京的馬路不夠寬,就調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說。
此后,長安街一直向1958年劃定的“紅線”努力。趙知敬說,現在很多地段,路寬已不止120米,“而這次大修,大劇院西邊這條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動。”
就這樣,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個“各方面認可的規劃”。然而,還沒來得及上報中央,就趕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規劃部門收到一個文件,明確提出“長安街建設暫停”。
東方廣場 的爭論
1985年,長安街規劃隨著改革開放后北京城的復蘇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長安街仍然是為了充分體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現代的情況,強調要有充足的綠化,還要有商業,把西單、王府井幾大商業中心聯系起來。”董光器說。
規劃做好了,卻沒有錢。在董光器的記憶中,長安街建設的再次啟動始于招商引資的大力推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開放加速,商業和金融機構開始在長安街扎堆。“特別是港商很看重長安街的地位,這樣,東長安街就蓋了很多寫字樓,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都跑到了西長安街。”董光器說。
隨著外資注入,長安街10年間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設量。也有人開始擔憂,長安街的政治意義在“軟化”嗎?
“作為神州第一街的長安街,蓋樓要經過資格審查。不是國家級的行政辦公樓,就是國家級的博物館、文化建筑。” 董光器說。
市場經濟的滲入,讓標準慢慢變化。據城建資料統計,長安街20世紀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屬于商業金融和寫字樓類的就占了14座,占總數的67%;而在5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17%。
為此,甚至有城市規劃者給北京市寫報告,要求堅持長安街的性質。90年代初,隨著體量巨大、玻璃幕墻的東方廣場突現長安街,爭議驟起。
“東方廣場原來設計的樓高是80多米,比規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棟建筑,寬488米,像一個大屏風。”趙知敬回憶。
1994年,趙冬日、張開濟等6位學者聯名提出,東方廣場大廈如果按照原方案實施,將改變舊城平緩開闊的城市空間。在此前后,北京市召開了一個東方廣場方案的展示會。
然而,規劃界人士依然無法認同這個突破心理底線的規劃。一位規劃人士表示,把東方廣場鑲在長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孫子輩”。
問題最終反映到中央,東方廣場大廈在開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論證,“一整棟建筑變成三組,高度分別定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的推動下,東方廣場作了再一次妥協,把高度降低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說。
其實,這樣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長安街的規劃。“知名開發商想把寫字樓蓋在長安街上,各區又急于招商引資,自然擋不住這股潮流。”董光器說。
拆了3000面廣告牌
世紀之交,長安街邊又起“拆廣告行動”。
1999年炎夏,也是國慶50周年大慶前夕,長安街上的廣告已相當“繁榮”,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兩側建筑頂部的廣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負責“拆廣告”的是時任長安街及延長線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主任趙知敬。在規劃圈里折騰了大半輩子的他,決定“下大力氣”讓長安街的建筑恢復原有的輪廓。結果,行動剛剛開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說長安街上的廣告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表現,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鄧小平路線。”趙知敬告訴《望東方周刊》。
不過,“上綱上線”沒見效。廣告牌和匾額最終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時間,經常有人來找我說情。每一個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來有朋友告訴我,有人恨得想摘我點器官什么的。”趙知敬笑道。
2002年,趙知敬組織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完成了《全面建成長安街、完善天安門廣場》的課題。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此次規劃邀請了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兩家大學,對長安街的行人展開社會調查。在問卷設計中,記者看到有“你對現在的長安街有什么感覺,有什么覺得不舒適的地方”這樣的問題。
回答五花八門。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對長安街的意見。”趙知敬說。
這樣的規劃思路,是否會讓這條寬闊威嚴的街道,更加親切而生動?
進了院門往里走,走過搭建在路旁的一間窄窄的廚房,就是王大媽的住房。房間里有一張床、一張沙發、一張方桌和一個柜子,柜子里放著些鍋碗瓢盆,中間是一臺21寸舊彩電。
王大媽的日常生活都集中在這間房子里。她已經習慣了周圍的一切,包括每隔四五分鐘地鐵一號線給地板帶來的明顯震動。
離別總是難舍。“這兒多安全啊!”王大媽說。
在這里,晚飯后,王大媽可以悠然地到天安門遛彎兒;白玉蘭盛開的季節,她可以賞賞長安街上的玉蘭花;在這里甚至可以不用鐘表,因為斜對面電報大樓每到整點就會敲起響亮的鐘聲??
持續了幾十年的生活節奏,就要改變。
4月1日,西長安街道路拓寬拆遷工程進入施工階段。這一項目位于西城區西長安街新華門南側,東起石碑胡同,西至中組部辦公樓,北起長安街南沿線,南至西安福胡同、東安福胡同西段、東安福胡同東段南延50米。拆遷范圍內共有居民 778戶,單位42戶。
“這是唯一一段現存的老北京的長安街。”著名文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老字號的揖別
“六福居”是一家老餐廳,位于大六部口西北角。由于緊鄰長安街,這家飯館的生意一直不錯,經常需要等座。
4月初,本刊記者來到這里,餐廳已經搬離,大廳空空如也,“六福居”三個大字的“六”和“居”還在,“福”字卻已不見。旁邊一位老居民說:“這是把‘福’帶走,叫‘留福’呀!走到哪里,生意都能做得興旺!”
第一批搬離的還有攝貿金廣角,這是一家國營攝影器材店,上世紀80年代由崇文門搬到此地,被譽為京城第一代攝影發燒友的搖籃。
搬遷后,攝貿被拆分為幾部分,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距舊址不遠的北新華街6號。本刊記者找到這家新店的時候,攝貿金廣角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司長寶正在忙著進貨,安排新店的工作。“這一處的營業面積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他說。
至于有著102年歷史的西長安街郵局,如今已成平地。緊隨其后正在搬遷的,還有柳泉居豆包專賣店、老百信大藥房、張瑞林書法藝術院等。
處于拆遷區的安福胡同里流傳著兩段歷史故事。清朝乾隆皇帝寵愛來自新疆的香妃,因民族習慣不同,香妃不便住進皇宮,乾隆將她安置在寶月樓(今新華門處)居住。為了讓香妃能望見族人,以排遣鄉愁,乾隆安排香妃族人聚居在西長安街路南的街巷中,即今東安福胡同一帶,時稱“回回營”。
《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三載,乾隆御制寶月樓詩云:“鱗次居回部,安西系遠情。”據老居民介紹,胡同里原有一座清真寺,如今已經殘破,深鎖在一個院子里。不過如果在胡同里細心尋訪,仍可看到數百年前回部建筑的遺存---一段漢白玉拱門,拱門上精美的雕花,流露著濃郁的伊斯蘭風情。
北洋軍閥時期,安福胡同曾是盛極一時的段祺瑞(皖系)軍閥政治集團的大本營。1917年11月,段祺瑞為了進一步鞏固他的政治,在安福胡同布置了一個龐大的房舍,作為他那一派軍閥政客聚會之地,起名叫安福俱樂部。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政客就叫“安福系”。由這個派系操縱選舉的議會叫“安福議會”。這個派系控制北洋政府,從民國六年(1917)到民國九年(1920)。民國九年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失敗,安福俱樂部被封。
專家感到撓頭的花墻
安福胡同附近有許多名字帶“栓”字的胡同,如北小栓、南小栓、東小栓等。這與明代宮廷制度有關。明代,官員上朝、辦事,有的會騎馬來,但是宮廷中大臣不得騎馬,因而絕大多數的官員都要在長安右門外下馬、拴馬。直到今天,在胡同里走走,偶爾在民居的墻上還能看到拴馬環,斑斑的銹跡訴說著歷史過往。
不過,文物專家說,這個地段總體上文物價值不高。讓文物專家最感撓頭的是,如何處理矗立在這片民居與西長安街之間的那段灰色花墻。
這段長200米左右的花墻大有來頭。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政府接管了清室的西苑三海,并將中海和南海作為總統府,從那時起,中海和南海被合稱為“中南海”。
按中國傳統,府邸的正門要開在南面。袁世凱為了顯示總統府的規格氣派,將位于中南海南墻內僅幾米處的寶月樓下層當中三間打通,改建為大門。又將擋在門前的皇城紅墻扒開一段缺口,加砌了兩道“八字墻”,使缺口與大門銜接。改建后的寶月樓,被命名為“新華門”。
當時,新華門對面是一片雜亂破舊的老房,為改善總統府前的觀瞻,便砌筑了這道西洋式花墻。
這一系列工程,都是由當時的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朱啟鈐主持的。“墻與新華門之間的比例非常協調,設計很高明,突出了中南海。如果拆掉,新華門看上去會變小。”謝辰生說。
如何處理這堵保存十分完整的花墻,謝辰生說目前仍在研究中。一個方案是整體往南遷移,另一方案是原地保存。
中國著名古建筑學家羅哲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新的規劃如果說避不開這堵墻,搬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可以回避,就原地保護。好在目前并沒有人主張要完全拆除這堵墻。”
4月14日,本刊記者看到,花墻旁長安街邊的槐樹已經被砍伐。“太老的就不要了,樹齡小的會移到別的地方。”
高度重視的拆遷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孟慶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次采取政府主導的拆遷方式,由政府成立拆遷指揮部,統一指揮協調。
“工程與建國60周年慶典沒有必然聯系。”孟慶利說,該項目完成后將全面實現長安街整體規劃,提升交通承載能力。“長安街新華門段由于路窄,經常出現擁堵。拆遷完成后,這一段將由目前的雙向8車道拓寬為雙向10車道,交通將得到改善。”
在拆遷補償上,孟慶利介紹,此次拆遷首次按市場評估價格進行貨幣補償,評估經過專家認定,并得到市主管部門批準。本次拆遷區域內所有住宅房屋的補償基礎價格為每建筑平方米30706元。
為鼓勵居民在規定期限內盡早騰退房屋,拆遷指揮部還對提前搬家的居民采取獎勵措施。在4月6日前搬家騰房的居民,每戶給予提前搬家獎勵費2.5萬元,重點工程配合獎勵費5萬元,合計7.5萬元。
考慮到拆遷居民需要一段時期的搬家周轉,拆遷指揮部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標準進行一次性補助。拆遷居民還可獲得其他補助,包括移機費每部電話補助235元,有線電視費每戶補助300元,空調移機費每臺補助400元以及住宅房屋每平方米20元的搬家補助。另外,殘疾戶家庭和低保家庭將各得到3萬元補助。
4月10日,獎勵期已結束,孟慶利告訴本刊記者,簽了拆遷合同的大致是一半左右。
王大媽還在猶豫,“我的房子面積是28平米,按照補償價格我沒法在周圍地段買房子。”
孟慶利介紹,指揮部籌集了三處限價房源供被拆遷居民選購,分別是昌平區東小口的溪城家園(均價6500元/平方米),朝陽區常營的富力陽光美園(均價5900元/平方米),海淀區上地的美和園(均價6600元/平方米)。此外還提供了部分二手房、商品房等房源信息。
“那都是五六環以外了。”王大媽說,一個人住到郊區,看病不方便。她沒有退休金,因而算賬格外仔細,“住樓房要交物業費,用抽水馬桶還得交水費,樣樣都需要多花錢。”
據本刊記者了解,這個地區整體居住條件比較落后,戶均住房面積不足20平米,目前已經搬走的居民大多是拆遷面積較大的或者已經在其他地方購房的。
一條顯赫大街的60年
一項面對長安街行人的問卷調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
《望東方周刊》記者李靜|北京報道
1950年6月,為迎接新中國第一個國慶日,“林蔭大道”工程在長安街熱火朝天地開始了。根據規劃,從東單路口到西邊的府前街東口,在原有15米寬的瀝青路南北兩側,各修一條15米寬的新路,新路與舊路之間,種上了四排高大的喬木。
“當時我們參加拓馬路,還在王府井砌高臺,有兩三米高,同時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規劃學會理事長趙知敬,當時才上初中,作為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也參加了修建大道的“義務勞動”。
此時,一幅關于“長安街如何建設”的規劃藍圖也慢慢展開。
請蘇聯專家幫忙規劃
“解放后不久,蘇聯專家先做了一次規劃,圖畫得特別簡單,就一大條。”原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董光器翻開城建檔案,指向1949年蘇聯專家設計的長安街行政建筑設計圖。其中,蘇聯專家提出,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并沿長安街建設行政辦公樓。這一規劃的核心思想是將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區。
這一設想卻遭到中國本土專家的反對。1950年,梁思成、陳占詳刊印長達2.5萬字的“梁、陳方案”,其中特別提到沿長安街蓋行政大樓這種模式存在種種弊端,建議在西郊發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這樣,圍繞著‘行政中心區位置’的討論,全國建筑師聚集到北京,反復做規劃方案。”趙知敬回憶說,整個5 0年代對長安街的規劃,雖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紡織部、燃料部、工業部在蘇聯專家提議的空地上一一開工。隨著經濟形勢好轉,“今兒蓋一棟樓、明兒蓋一棟樓”。
北京急需一個整體規劃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聘請蘇聯專家指導。6月下旬,又指定了幾位老干部,抽調少數黨員青年技術干部,研究這個問題。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報了統一的城市規劃意見--- 《改建與擴建北京規劃草案要點》。
行政中心最終被確立在舊城,長安街作為“中央主要領導機關所在地”被明確提出。但長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規劃委員會工作的趙知敬回憶,那時,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規劃專業。于是決定邀請蘇聯專家來做詳細規劃。“我們當時就聽蘇聯專家講課,每天看蘇聯的教科書。”在“蘇聯專家結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
在這份方案中,長安街的藍圖基本繪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為“全國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長安街則肩負起全力體現這一主題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門和有全國意義的重大建筑,將沿長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馬路主義”
1958年方案的執筆者之一、時任北京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圖室主任的陳干,對長安街作為北京“東西軸線”的建設,滿心憧憬。他希望通過長安街的規劃,形成有別于紫禁城的軸線,與傳統的南北軸線相交于天安門廣場,確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點”(城市坐標)。
在趙知敬這些老北京心中,長安街能作為“東西軸線”是由它的歷史地位所決定的---它是北京舊城最寬的一條東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臨近天安門廣場。
長安街在歷史上正式的長度只有3.8公里,從東單到西單。“東單往東到建國門,西單往西到復興門都沒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幾個彎,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寬度。每天公共汽車在里面滿滿當當地開著。”趙知敬回憶說。
這樣的格局在1958年被徹底改變。國慶十周年前夕,西單到復興門的邱祖胡同等,東單到建國門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寬的瀝青路,復興門到建國門全線貫通,長安街長長了---6.7公里。道路徹底打通,為兩側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十年大慶為長安街的建設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在董光器看來,如果只有3.8公里,長安街根本沒法進行大規模建設。
在大規模建設的同時,一個禁區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動。事實上,從1952年拆除長安左門和右門開始,“古建筑的拆與保”的交鋒就在不斷上演,當長安街向著具有“首都風貌”的大干線思路發展,雙塔寺、牌樓這些古跡,都隨著不斷翻新的長安街景象,走入歷史。
由是,長安街的改造,在關注北京城變遷的記者王軍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槍”。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長安街呈現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長安街修起了80米寬的游行大道,擴建后的天安門前,形成了東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廣場---這種規模和氣勢,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象。
此時,長安街沿線的建筑,除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飯店、民族宮等,還有在長安街南邊的紡織部、煤炭部等部委辦公樓。這些莊嚴而肅穆的大廈,隨著國慶10周年,完成了長安街從規劃草圖走向現實的轉變。一條以政治形象聞名世界的大街,從此誕生。
然而,“第一槍”打出沒多久,便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來,國家大劇院沒建成,科技館也撂下了。”董光器回憶。直到1964年,經過三年調整,國力有些恢復。萬里作為北京市當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匯報,提出中央有一些辦公樓可以集中在長安街上蓋。
很快,北京市政府開始著手編制長安街規劃。1964年4月,長安街有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方案,特別是確定了包括道路寬度在內的具體原則。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長安街的馬路寬度一直難以確定。“50年代翻譯很多國外首都的資料,感覺到,作為首都的一條主要街道,道路過窄對交通影響很大。所以,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提出北京的馬路要寬。”
國家計委與北京市委的意見相左,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但北京市委的態度堅決,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會上表態:你說我是大馬路,我說你是小馬路主義。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是太寬,現在北京的汽車還不太多,等你們這些年輕人到八九十歲,北京有幾百萬輛車的時候,再看誰對誰錯。
到1954年,對長安街寬度有了初步定論: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終劃定為“120米”。“北京派出一個城市建設代表團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區的建設,回來一比較,發覺北京的馬路不夠寬,就調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說。
此后,長安街一直向1958年劃定的“紅線”努力。趙知敬說,現在很多地段,路寬已不止120米,“而這次大修,大劇院西邊這條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動。”
就這樣,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個“各方面認可的規劃”。然而,還沒來得及上報中央,就趕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規劃部門收到一個文件,明確提出“長安街建設暫停”。
東方廣場 的爭論
1985年,長安街規劃隨著改革開放后北京城的復蘇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長安街仍然是為了充分體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現代的情況,強調要有充足的綠化,還要有商業,把西單、王府井幾大商業中心聯系起來。”董光器說。
規劃做好了,卻沒有錢。在董光器的記憶中,長安街建設的再次啟動始于招商引資的大力推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開放加速,商業和金融機構開始在長安街扎堆。“特別是港商很看重長安街的地位,這樣,東長安街就蓋了很多寫字樓,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都跑到了西長安街。”董光器說。
隨著外資注入,長安街10年間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設量。也有人開始擔憂,長安街的政治意義在“軟化”嗎?
“作為神州第一街的長安街,蓋樓要經過資格審查。不是國家級的行政辦公樓,就是國家級的博物館、文化建筑。” 董光器說。
市場經濟的滲入,讓標準慢慢變化。據城建資料統計,長安街20世紀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屬于商業金融和寫字樓類的就占了14座,占總數的67%;而在5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17%。
為此,甚至有城市規劃者給北京市寫報告,要求堅持長安街的性質。90年代初,隨著體量巨大、玻璃幕墻的東方廣場突現長安街,爭議驟起。
“東方廣場原來設計的樓高是80多米,比規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棟建筑,寬488米,像一個大屏風。”趙知敬回憶。
1994年,趙冬日、張開濟等6位學者聯名提出,東方廣場大廈如果按照原方案實施,將改變舊城平緩開闊的城市空間。在此前后,北京市召開了一個東方廣場方案的展示會。
然而,規劃界人士依然無法認同這個突破心理底線的規劃。一位規劃人士表示,把東方廣場鑲在長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孫子輩”。
問題最終反映到中央,東方廣場大廈在開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論證,“一整棟建筑變成三組,高度分別定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的推動下,東方廣場作了再一次妥協,把高度降低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說。
其實,這樣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長安街的規劃。“知名開發商想把寫字樓蓋在長安街上,各區又急于招商引資,自然擋不住這股潮流。”董光器說。
拆了3000面廣告牌
世紀之交,長安街邊又起“拆廣告行動”。
1999年炎夏,也是國慶50周年大慶前夕,長安街上的廣告已相當“繁榮”,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兩側建筑頂部的廣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負責“拆廣告”的是時任長安街及延長線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主任趙知敬。在規劃圈里折騰了大半輩子的他,決定“下大力氣”讓長安街的建筑恢復原有的輪廓。結果,行動剛剛開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說長安街上的廣告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表現,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鄧小平路線。”趙知敬告訴《望東方周刊》。
不過,“上綱上線”沒見效。廣告牌和匾額最終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時間,經常有人來找我說情。每一個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來有朋友告訴我,有人恨得想摘我點器官什么的。”趙知敬笑道。
2002年,趙知敬組織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完成了《全面建成長安街、完善天安門廣場》的課題。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此次規劃邀請了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兩家大學,對長安街的行人展開社會調查。在問卷設計中,記者看到有“你對現在的長安街有什么感覺,有什么覺得不舒適的地方”這樣的問題。
回答五花八門。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對長安街的意見。”趙知敬說。
這樣的規劃思路,是否會讓這條寬闊威嚴的街道,更加親切而生動?